,
缘 起
登山有多种方式, 一直以来,我偏爱简洁的阿尔卑斯式, 只是从未简洁到单人solo的程度。
对于solo,我内心有抗拒感。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 人的认知可能发生一些变化, 去推翻之前的想法。

一次,在勒多曼因带商业活动中途中,我突然看到一个山,5000多米。 不是很难,但对我很有吸引力,这种感觉很微妙。因为不难,和谁搭档好像都差点乐趣…反复想了很久,solo的念头突然冒出来。
做决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我和一些攀登者交流,我分析最坏的情况: 情况一旦发生,有什么后果? 这个后果是不是我能接受的?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,我需要做哪些准备?
我知道这次攀登难度不会大,没有很极限,不会让我有明显的突破,但大概会带给我内心的变化。
拍 摄
目标确定后,在一次偶然交流中,了解到《舌尖三》的拍摄团队想制作一部分我个人的纪录,其中攀登的镜头,希望借这次机会拍摄。
于是自己一个人的行动, 就变成了一次拍摄solo的行动。 相对简单的事情,现在又变得复杂且人多了。
由于各自空闲时间有冲突,最初制定的时间后推,实际出发时间是2021年的11月22号,这之前两天,正遇到全国范围的大降温。
下了大雪,刚出发就被雪坡阻在了路边。 本来车辆可以直接开到格西草原,现在嘛,乖乖徒步两个小时,才到了原定的徒步起点。


大量拍摄也减缓了我们的行进速度,一天到上日乌且的计划只能搁浅。 实际上,第一天到达两岔河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了,到了营地还需补拍许多镜头,攀登日程随之修改。
拍摄团队多年没有进到这里,好像觉得,雪后的日乌且沟,到处都是景。 也许是好看的, 只是我有点看麻木了。

第二天,到达上日午且的牛棚,又在雪地里来回反复的拍摄。想拍好片子,确实要一番费时费力的工作。

▲路遇鬣羚?
近几天的低温和降雪,让整条沟一片纯白,牛棚主人已经把牛赶到了更低的地方,这里空无一牛。
之前驮马能继续往前,走到海子边。 不过现在,需要从牛棚开始靠人。团队里六个教练一起运输,每个人除了自己的攀登装备外,还背一个大摄影包。

▲年轻人不怎么喜欢穿衣服。
负重让大家的行进变得缓慢,而由于行动缓慢,就需要背更多的食品,又意味着更大的负重量。
2天后,我们抵达了计划的线路附近。 营地建在4800米的冰川上,这个位置正好可以完整的观看我攀登的全部过程。

攀 登
第5天的时间,真正属于我自己。
早上3点,被闹钟叫醒,满怀睡意。45分钟后离开帐篷,按照自己节奏行进。
我评估过每一段要用的时间,计划在天亮之前到达技术路段根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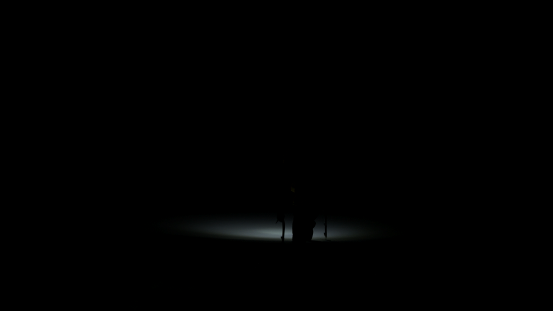
出发1个小时后,我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节奏,这让人很享受。
不用结组,不用等待谁,不用时常做保护点。同时也要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,包括一个人过冰川裂缝区,一个人判断方向和路径。
日出前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无法清晰的知道我的目标在哪个方向。到冰坡下方时,我比估计的晚了四十分钟。
后面的攀爬,则比我预想的高效很多。线路比我正面看去要陡,但冰雪整体的状况很好。


▲在山体上,我比蚂蚁还小。
到了中间的平台,我只短暂的休息,调整了一下呼吸就继续攀爬。 早上9:40,我到了山顶。

风很大,吹得我心慌,我有点担心被吹下去。身体开始哆嗦,逐渐难以控制。我需要尽快下降到低一些的位置。
顶峰的冰雪很硬,如果做保护下降,需要很多时间。于是我开始倒攀。 很快,大概十几分钟,我下降到了顶峰下一百多米的平台上稍作休整,以让身体停止颤抖。
接着就继续下降,大多数时候就是倒攀。不到一小时,就撤到了平缓的冰川上。
由于太快的消耗,我的身体开始虚弱,缓慢行走了一会儿,才意识到了自己能量供给不足,想起要吃东西,喝水。 快1个小时后,身体开始恢复。
我呼叫营地的小伙伴们收拾东西准备下撤,6点多大家回到了上日乌且的牛棚。 第六天,从直接回成都。至此攀登结束。
攀登当天,爬升800米左右,下降1400米,共用时15个小时左右。 技术路段为65°-70°冰雪坡,长度300米,准备了绳子,冰锥等装备,但没有用到。
手表记录的爬升数据:
总 结
我自认不是一个多胆大的人。 入攀登圈十几年来, 我虽登顶了贡嘎,但从未触碰过solo。
我可以不问名字、不关心海拔、也不管什么方式,只在乎我是否想攀登这个山。但如果我想登,那不但要完成目标,还要全身而退。
对我来说,solo的风险级别完全不同,给人的心理压力也不同...很多次,我带着初学攀登的客户结组。我先锋、他们打保护,很难说这个保护有多大作用,但有、和没有,那就是不一样。
单就这次攀登来说,我是很开心、很享受的,一切靠自己控制,没有外界影响,非常随性自由。但当全世界好像只剩下自己一个人,又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仓惶、孤寂。
我觉得solo更需要缓慢的成长过程、内心的蜕变,需要更稳定的心态,才能确保自己安全,但心态这件事,哪有那么好控制呢?
所以我个人到现在为止,也不提倡solo, 只是我自己也会想尝试。
人也许永远要在矛盾中,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攀登路上,我也尚在寻找之中。

|